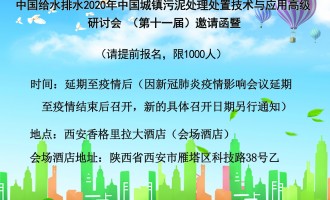“陽光老總”與“陽光班”的孩子們

袁立在清華大學對學子們說:“人生就是一個圓……”
“近60歲的人,可以談談人生了吧。”袁立說。語氣里,有一種舉重若輕的灑脫。之所以聽著舉重若輕,是因為后面還有一句:“談人生,一個平民百姓與一個億萬富翁,誰更有說服力?”
這是數小時的采訪中,袁立唯一一次提到“億萬富翁”這個字眼。更多的時候,這位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倒像思想者,侃侃而談著他的種種理念,關于讀書、關于責任、關于管理、關于人生——
讀書,最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有經濟學家統計過,中國民營企業的平均生命周期僅2.7年(發達國家是7.9年)。而“富大”,自1992年靠20萬美元起家,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一路走到了今天——擁有八個子公司的集團型制造業民企,年產值超過4億人民幣,納稅千余萬元,成為全國膠帶行業的佼佼者。
回顧十幾年來走過的坎坷、創下的業績,袁立感慨,是讀書使他有別于旁的民企老板,使他的企業具備了戰略管理意識,從而傲然立于行業領先地位。
“一個人所能受到的最好教育,來自父母。”他說。當他開始懂事的時候, 母親就不斷地從供職的銀行借書回家,從連環畫到各種各樣的小說,從科幻小說到歷史小說。印象最深刻的,是《契柯夫中短篇小說選》中的那篇《打賭》,小男子漢為道德的力量所震撼。“母親讓我養成閱讀習慣,我不知不覺地成為一個終生閱讀者,這對我以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長大了,因“文革”失學,當工人、跑銷售,是書照亮了暗淡而漫長的青春歲月。企業走上正軌之后,安定下來的老總袁立尋回了兒時的好習慣:每天看書兩小時。由于不甘心,這當年的優等生在業余時間,讀高三,上大專、本科,一直到2001年修完MBA,還打算繼續念博士。不是世俗的為文憑去鍍金,全是非常學以致用的學習,“所以,我能夠接觸到世界上最新的一些理念、思想,為我的企業所用。”他把有關經濟的讀書心得寫成文章,每月一篇,發表在企業報上,與同道分享。《中國的民營企業生命周期為什么那么短》、《中國的民營企業如何實施戰略管理》、《中國民營企業家為何總是曇花一現》、《培訓很貴,不培訓更貴》、《合作雙贏——企業戰略管理中的白金法則》……這些真知灼見的結集《路漫漫兮——試論中國當前經濟走勢及富大戰略決策》,在行業內外一時頗為搶手。
很自然地,袁立想做善事回饋社會,他的目光鎖定了教育。“人有先天的優秀秉賦,但是學成之前,誰也不知道哪個是人才。如果一個人由于經濟原因而輟學,沒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天才,對我們的國家、民族都是損失。我不敢說我現在幫助的這七八十個學生里面將來肯定會出現中國的牛頓或者愛因斯坦,但是我覺得這些孩子中有許多確實是很有天賦的。”幫助貧寒的孩子完成學業,他有個形象的比喻:讓窮人家具備造血功能。讀書,最能改變一個人、一個家庭的命運啊!
1996年設立的“富大幫困基金”,每年投入五六十萬元,主要用于教育事業,至今已達750萬元。那些讀不起書的孩子,因了袁總的一句“窮不要緊,但要有志氣。富大會幫助你們讀到大學畢業的”,舒展了愁眉,專注于學業了。
最新一期的《富大報》上,登載了一封致袁總的信:“每天,當我用拐杖撐著走上二樓教室時,雖感到如此困難重重,但我的腳步卻是堅韌不拔的。因為在我的身后,有著袁伯伯您與社會上所有關心我的好心人,在催我奮進,使我每天都倍感自信與充滿希望……”寫信的李蔚箐,在首屆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中,獲得了上海市一等獎、全國二等獎。
財富越多,社會責任也就越大
“陽光老總”的雅號,出處在“陽光基地”。
那年,袁立結識了華東政法學院的肖建國教授。肖的研究領域是青少年犯罪。聽他披露,我國青少年犯罪重犯率高達70%。袁立大吃一驚,忙問怎么會。
“他們回歸社會以后,因為學歷較低,加上有污點,沒有人愿意招聘。最后為生活所逼,一部分人重新走上了犯罪道路。”
“你研究了這么多年,有什么解決辦法嗎?”
“國外有些好的經驗,比如‘中途之家’,就是政府花錢,讓一些丁克家庭收留刑滿釋放的孩子,給他們一個正常健康的環境,逐步逐步地感化他們,幫助他們慢慢回歸社會。”
“讓我的企業作為你說的這個‘中途之家’吧,企業容量大啊!”
兩人激動地合計著,找到虹口區檢察院。商量下來,就把那些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又可挽救的孩子放在“富大”,讓他們在半工半讀中完成改造。“陽光基地”,一個比“中途之家”更充滿希望的地方,就這樣誕生了。
后來,有研究者評價:“富大企業的探索成果,實際上給我們現在的社區矯治提供了很好的建議。‘富大’的可貴之處在于,不是搞一兩次活動,一年兩年就沒有了,而是從1996、97年一直延續到今天。”
袁立則想得更遠。他感到,企業如同一棵生長在自然環境里的植物,是土壤、陽光、雨露、空氣等提供了其生存的養料。你這個企業老板會賺錢,成了一棵大樹,如果這棵大樹在擴展過程中,只知消耗資源卻不向環境提供幫助,甚至破壞自然生態,那么這棵樹也活不長久。這個自然的因果關系同樣是適合企業的生存法則。企業在財富積累中,要消耗人力資源、能源、交通設施,包括土地、廠房以及政府、社會提供的各類服務等。回報社會不僅是企業的責任和義務,也是企業不斷發展的生存之道。他得出的結論是:“占有財富就是占有資源,就意味著承擔責任。財富越多,社會責任也就越大。”
所以,除了“陽光基地”,還有“陽光班”——袁立的母校繼光中學,地處勞動人民聚居區。四年前,“富大”召集起44名家境貧寒的孩子,組成“陽光班”。從此以后,他們的開學典禮、主題班會、運動會,他們的中秋節、端午節,都沐浴了 “富大”的陽光。每年一度“富大兒女回家過年”、每個雙休日集體家教……“陽光班”在學習音樂、書法、美術,提高綜合素質、全面發展的同時,成了年級組的總分第一、虹口區的先進集體。還有兩批各10名貧困學生——“富大”包下了他們從小學到大學的學費、代辦費、校服費、活動費,“富大”人跟他們談人生、談理想、談感恩、談奉獻,每逢暑期“富大”就是大學生們的實習基地。還有培養了不少圍棋好手的虹口區一中心小學圍棋俱樂部……
這么多年過去了。“陽光基地”收治的16名失足青少年,回歸社會后,絕大部分反響很好,有個學烹調的年輕人還在巴西開了中餐館。10年前,“富大”承諾“跟蹤資助”的10名貧困孩子,已有9名考進大學,其中2名入了黨,5名成為上海市、區三好學生。“我們把這些都看成企業發展的組成部分。” 袁立表示,“富大”是把社會公益作為企業發展的項目之一來做的。每年在造預算時,都會根據企業發展規模制訂這個項目的資金規劃,而不只是拿出一筆錢一捐了事。
袁立信佛。信佛的人相信好心有好報?“有些人,很功利、很利己地燒香、拜佛,那是沒用的。”他笑笑,講了一個故事:“陽光基地”的事跡通過上海電視臺轉播后,感動了遠在安徽馬鞍山的馬鋼公司上上下下。那回,“富大”到馬鋼去簽一個訂單。那兒的人一聽“富大”,就說我們知道啊,你們辦了個“陽光基地”。人家對“富大”印象很好,“富大”很順利地就拿到了訂單。“做善事的時候,沒想過要回報。但你無私奉獻了,其中的因果關系卻是絕對存在的。”
沒有信仰的市場經濟,走不遠
“有信仰的市場經濟”,就是人心向善,有前途。“沒有信仰的市場經濟”呢?就是物欲橫流,人都鉆在銅錢眼里,成為心靈空虛的拜金主義者,社會對個人沒有制約,主流價值觀模糊,怎么會有前途呢?袁立好惡分明:“我不喜歡沒有信仰的人。”對于小環境,他很理想主義:至少,在“富大”,大家應該都是有信仰的。
“富大”招人,標準很特別:開宗明義就要求,孝敬父母。袁立加注:“一個不具備感恩心態的人,情商肯定極低。在一切感恩之中,對生你養你的父母的感恩之情是最深的。連這點都做不到的人,不會是好人。” 然后,再要求兩條:與人為善,助人為樂;講究誠信。有了這三條,才算好人。經過培訓,成為“好人+能人”,才是合格的“富大”人。每一個進“富大”的新人,翻開《員工守則》,就會讀到“公司理念:富大為人人,人人為富大”、“企業文化:善待用戶,善待員工。來自社會,回報社會,回歸社會”。袁立告訴他們:“兩個‘為’、兩個‘善待’,概括起來就是兩種理念,一是雙贏,一是以人為本。”
有一次,他去拜訪員工,“進門只覺得渾身發冷,像到了沙漠,因為那個家連一張報紙都沒有的。”回到公司,他為所有中層干部的辦公室配了書櫥,希望他們自覺買書、讀書,讓讀書像吃飯、睡覺、娛樂一樣融入生命的每一天。
這個整天思想著的老總,希望與他的員工分享自己的價值觀,希望有一天更多的員工能夠認同他的價值觀。他甚至“立志要把‘富大’辦成一所大學校,我也下定決心當好校長”。長假過后的第一天,是公司法定的員工培訓日,每年三次,雷打不動。在企業里,他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企業文化,核心就是孔孟之道,就是儒學。“中國人的平均智商要超過美國人、日本人,為什么總是落后于人?”他判斷,“是情商出了問題。”他不斷地、苦口婆心地灌輸,回報社會、幫助弱者是企業文化的一部分。
熏陶的作用,終于顯現了:在不久前公司的一次民意調查中,超過98%的員工認為,公司每年舉行的社會慈善活動很有意義,是企業的一份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形象。
1998年的一天,袁立路遇老同事。對方不理解:“你現在自己是老板了,還為誰這么賣力?”這一問,引發了他的思考:是啊,我這么多年起早貪黑為企業建功立業,為何從未有人評我當先進?答案不言而喻:我是老板。老板就是沒有名份的標兵。悟出了個中道理,他的經營理念也隨之大變:要讓標兵都變成老板,讓大家共同富有,讓更多的人來當家理財,一起把企業搞大。他拿出1000萬元股份,把其中的20%贈給中層干部和標兵,公司的老板由1個變成了10個。三年后,增值到了5000萬。
袁立介紹:“這叫MBO(Management Buyout),管理層收購,通過收購使企業的經營者變成所有者。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歐美國家就流行了。”他修改了一句中國俗語來詮釋MBO:小河有水大河滿。
在“富大”培養200個百萬富翁、20個千萬富翁,讓所有員工在10年內居有房、行有車。這是袁立10年前繪就的財富藍圖。如今,公司已經孕育了30多個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也悄然出現了……
人生,就是由淺入深、由深入淺
1950年,袁立出生于上海一個普通的銀行職工家庭。小學時,他一度天天把貧困的同桌帶回家吃午飯。他在社會上行善,是賺到了“第一桶金”就開始的。
如今,頂著民革服務全國先進個人、上海市勞動模范、上海市慈善之星和虹口區政協常委、虹口區工商聯副會長、上海市未成年犯假釋基地站長等榮譽或頭銜的這個人,還珍藏著創業時為審批圖章跑過整整一年、送過貨、拉過外地客戶的一部兩輪摩托車,珍藏著當年的一張小辦公桌、一把銹跡斑斑的折疊椅。最早的外地客戶退休了,來上海玩,跟他吃頓飯、敘敘舊,順便對人吹噓“袁總親自開摩托車拉過我”。采訪到中午,他照常回家陪母親吃飯。他愛穿松緊口的布鞋、戴100多元的天梭電子表,“一個人為別人活,才時時關心別人怎么看自己,才需要各種裝門面的東西。有的人用勞力士、寶馬包裝,可三句話一說就露馬腳了。人還是要講內涵。”忽然有一天,他戒掉了每天兩包的煙,酒也很少喝了,因為“自己覺得一輩子的煙酒‘定額’大概已經用得差不多了”,而對事業的使命感又促使他保養身體,不光為了自己和家庭,還為了員工、公司、客戶、銀行、社會。
袁立的“財富與人生”主題演講,深受清華、北大學子的追捧。那些書生,何曾聆聽過這等貼切、有益的教導!比如,“人生就是一個圓,由淺入深、再由深入淺。”演講者以自己幾十年來交通工具的變化,瀟灑地寫照這個“圓”:最早是步行,然后是自行車、助動車、摩托車,一直換到轎車,桑塔那換成奔馳,現在上下班又騎回自行車、又步行。騎自行車到市政協開會,“走地面,走小路,一路上看見很多新的風景,心情很好。不像以前坐小車,出門上高架,什么都看不見。”
袁立也有嘆息的時候。“幫了這么多學生,想不到幾個大學畢業的都要求我們別再提幫困的事,免得影響他們的前途。唉!”像是自我安慰,他又喃喃自語:“沈強肯定不會這樣……后面這些學生也不會的……” 沈強,是他無意中幫助的兒時伙伴的遺孤。
曾經在箱根湖畔,袁立看日本人垂釣。魚上鉤后,那人在河灘上用尺量,魚長27厘米,遂放生。原來,法律規定不到30厘米的魚是不可以吃的。旁觀的他大為感慨:“人前人后、有人沒人一個樣。此人是為自己活。”這個故事,被他拿來為自己的善行作注腳:“我為自己活,所以做好事。”于是,不再提那些令人失望的大學畢業生。
他開始憧憬新的夢:辦一家圖書館和一所綜合性中級技術學校,都是公益性的、不收費的。
作者: 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