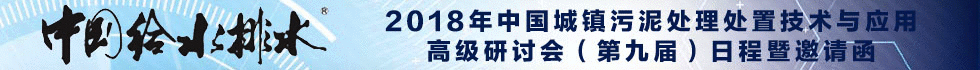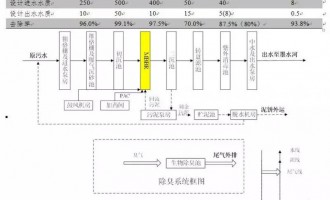---------行動故事----------
文-焦東雨(中國周刊記者)
陳立雯已先后把廣州市環保局和杭州市環保局告上法庭,四川省環保廳將是第三家。
與政府對薄公堂的行為,很難與一個80后女生聯系起來。可陳立雯就是——馬尾辮,黑框眼鏡,素面朝天,衣著普通,仍像是剛走出校園一樣。
身為師范院校英語專業的本科和碩士,她本可像絕大多數同學那樣,去尋一份安穩的教職,這也符合她父親的期望。但這都在一個春節里發生了逆轉。
陳立雯看了一期采訪環保組織“地球村”創辦人廖曉義的電視節目,深有感觸。隨后,她成為環保志愿者,并在畢業后成為全職環保人。
通過申請信息公開這樣的法律途徑干預污染,是她的工作內容之一,可環保之路并非坦途——幾乎每次申請都迂回曲折,申請、行政復議,乃至起訴……
“像擠牙膏一樣。有時,我感到瞠目結舌、啼笑皆非。”她說。
“他們就是不斷地推”
陳立雯目前供職于環保組織“自然大學”,主要負責垃圾處理,尤其是焚燒產生的污染等調查工作。
她申請垃圾焚燒信息公開始于謝勇的遭遇。謝勇是江蘇省南通市海安縣人,2008年,他的孩子出生不久,即被診斷為腦癱和癲癇。謝勇懷疑這與他家附近的海安垃圾焚燒廠有關,于是開始尋求該廠排污監測報告等證據。
海安縣垃圾焚燒廠于2006年6月開始運營,2009年10月就地擴建升級為垃圾焚燒發電廠。
2010年6月25日,謝勇提出申請,要求海安縣環保局提供垃圾焚燒廠建廠行政審批、環評報告、從投產到2009年秋的監測報告等信息。
《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規定,公民個人可向環保部門申請獲取政府環境信息。但海安縣環保局答復謝勇,環評和監測報告不屬于環境信息公開范圍,不予公開。
當年9月10日,謝勇在海安縣法院起訴海安垃圾焚燒廠,成為“中國首起垃圾焚燒致病案”。海安垃圾焚燒廠由此進入陳立雯等環保人的視野。
2011年2月23日,陳立雯向江蘇省環保廳、南通市環保局和海安縣環保局三級環保部門,同時提交了海安垃圾焚燒信息公開的申請。
申請公開內容包括:原垃圾焚燒廠環評報告及投產至2009年10月的監測數據和處理報告、新建垃圾焚燒發電廠及配套污水處理廠的環評報告及批復。
那是陳立雯第一次申請信息公開。她當時也不太了解該怎么做,還專門咨詢了謝勇的代理律師劉金梅。向三個不同級別的環保部門同時申請,難易程度高下立現。“比較明顯的感受就是,無論是郵寄材料還是在線提交,從縣級環保部門到廳級環保部門,越往上渠道會越通暢一些。縣級環保部門,就沒有在線申請通道。”
可申請的結果,則沒有本質不同。
《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要求環保部門應在收到申請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予以答復。但江蘇省環保廳和南通市環保局的答復均在15個工作日之后。
內容上,關鍵的環評和監測報告,則是省廳推給市局,市局推給縣局,還有就是推給建設單位和環評機構。“他們就是不斷地推,你推我,我推他。”
在陳立雯看來,海安縣環保局的回復尤其過分,“從形式上,我要求紙質回復,卻給了我一封電子郵件;從內容上,電子郵件正文沒有任何內容,只有一個附件,附件里只有一句話。”這句話是“海安縣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已于2010年9月15日取得江蘇省環保廳的批復。”
“我就火了,我很生氣!”——從此,這成為陳立雯描述信息公開這項工作時的口頭禪。
短兵相接
2011年4月,陳立雯前往海安實地調查,目的之一就是去找海安縣環保局,看他們為什么給出一個如此簡單、沒有任何有效信息的回復。
“去之前,我就跟他們的副局長溝通過。到之后,再打電話,他就說‘我不在’。但從樓下看,他是在的。我就去他們局辦公室,辦公室讓我去找宣傳科副科長。那位副科長要求我提供單位證明。我就問他,讓同事傳真給我可以嗎?他說可以。”
“下午兩點,我拿著傳真件又去找他,他卻說‘我怎么知道這東西是真的假的’……他們態度非常不好,所以我們決定走行政復議。”
《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規定,公民認為環保部門在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工作中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2011年4月底,陳立雯向南通市環保局提起行政復議,再次要求海安縣環保局公開環評和監測報告。“南通市環保局就施加行政壓力,要求海安縣環保局必須做出回應。復議,它就要有一個答辯”,可結果并不盡如人意。
5月10日,海安縣環保局就行政復議做了答復,A4紙寫了兩頁半的內容,援引《環境信息公開辦法》等法律條款,和監測報告涉及商業秘密,所以未做公開。
近身肉搏
2013年7月9日,陳立雯向成都市中院遞交了起訴四川省環保廳的訴狀。當時法院的接待人員就表示,“你這種情況可能就不能立案”。
陳立雯表示了質疑:“能不能立案,不能你一個人說了算吧。”《行政訴訟法》規定,法院接到訴狀,應當在七日內作出立案與否的裁定。可直到8月,陳立雯也沒有收到任何消息。
此時,陳立雯訴廣州市環保局的二審在廣州開庭,四川的事情暫時擱置。
廣州李坑垃圾焚燒廠2006年投產,此后一直引發當地居民對該廠污染致病的質疑。
2012年7月20日,陳立雯向廣州市環保局提交李坑垃圾焚燒項目信息公開申請,要求提供環評報告、監測報告等一系列文件。
按照15個工作日內答復的要求,廣州市環保局最遲應在8月10日回復,但陳立雯直到9月4日才收到簽章日期為8月31日的答復。答復稱環評報告不屬于政府主動公開的信息,建議向建設方或運營方索取;監測報告僅提供了部分排放物部分時段數據。
由于在南通對行政復議的軟弱無力深有體會,陳立雯決定這次直接提起訴訟。2012年10月30日,陳立雯給廣州越秀區法院寄出起訴廣州市環保局的訴訟材料,要求提供全部申請信息。
12月25日收到傳票后一天,陳立雯接到廣州市環保局的電話,問他們已經回復了,為什么還要起訴,陳立雯提醒他們先看看訴訟材料。
12月28日,廣州市環保局再次致電陳立雯,說補充回復已發到她郵箱,并會將書面材料快遞給她。但補充答復僅是對不能提供環評報告作了進一步解釋,補充了部分監測數據,仍有部分數據缺失。
2013年1月18日,陳立雯訴廣州市環保局案開庭。這是陳立雯的第一次行政訴訟,但她覺得事情自然發展至此,毫無緊張之感。
一審判決,廣州市環保局被確認答復逾期違法,但沒有對其拒絕公開信息內容是否合法做出判決。陳立雯認為是漏判了訴訟請求,也與她的訴訟預期相背離,于是向廣州市中院提起上訴。
8月6日,二審開庭。
廣州二審未出結果,對杭州市環保局的訴訟于8月20日開庭,陳立雯正在出差途中,只能委托同事出席。
杭州濱海垃圾焚燒項目,周邊居民一直有意見。“所以我們就協助他們做些工作,并申請公開環評、監測報告等信息。”杭州市環保局的回復與其他地方沒有兩樣,“監測數據向區環保局要,環評報告向浙江省環保廳要。沒了。把自己擇得一干二凈。”
“你得拿出證據”
起訴廣州市環保局一審之后的2013年3月,陳立雯又向廣東省環保廳提出申請公開李坑二期的環評報告等信息。李坑二期于2013年6月點火試運營。
在告知陳立雯將延期答復一次之后,廣東省環保廳于4月12日告訴陳立雯可到環保廳查閱。16日,省環保廳對陳立雯確認可現場查閱,免費提供全本復印。
最初,廣東省環保廳不許她復印任何信息。陳立雯認為,這是訴訟產生了影響。“因為一期的訴訟,他們也確實吸取了教訓,按照法定的日期來回復。廣州市環保局的官司出來之后,廣東省環保廳廳長表態,要尊重公眾的知情權。”8月7日,陳立雯到廣東省環保廳查閱、復印李坑二期環評。環評全本共600多頁,陳立雯兩個小時也沒復印多少。環保廳工作人員主動提出幫忙復印,請她第二天來取。
這是陳立雯就全國十多個垃圾焚燒項目提出申請以來,獲得的第一本環評全本。兩個月前,她還拿到三本部分環評報告全本。
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陳立雯再次向江蘇省環保廳在線提交信息公開申請,內容包括海安垃圾焚燒等項目的環評報告、監測信息共13項。
對方要求陳立雯一事一申請。照做之后,又說系統亂碼,讓陳立雯重新提交。
“你說亂碼就亂碼,你要我怎樣就怎樣,你得拿出證據呀。”陳立雯據理力爭。最后,對方說“你重新申請,我們以你第一次申請的日期為準。”
陳立雯重新申請,結果仍是不能提供環評等信息,她鍥而不舍,對方又辯解說要征求第三方意見。經過持續追問,陳立雯終于在2013年6月收到三本環評部分全本。這些信息得來太不容易了,“就跟擠牙膏似的,所以這些報告,我們一定要好好利用起來。”
三本環評中,涉及海安的僅是二期垃圾焚燒發電項目,但關于此前垃圾焚燒廠的環評和監測信息,陳立雯至今沒有拿到。
廣州二審的結果最終出來了,維持原判。對于這個結果,陳立雯考慮上訴的同時,再次向廣州市環保局提交了相關監測信息公開的申請。
廣州市環保局在15個工作日內答復了,但沒有效仿其上級單位,反而要求陳立雯出具其申請信息與工作相關性的證明。“按照法律規定,我以個人名義申請,不需要提供這些信息。他們開始設置障礙了。”陳立雯考慮再次提起訴訟。
杭州的訴訟,目前通知陳立雯說,案情復雜,要延期到2014年1月再做裁決。
對四川省環保廳的起訴,立案就頗費周折。先是成都中院裁決不予立案,陳立雯上訴到四川省高院,高院又裁定應當立案。
2014年1月2日,陳立雯收到成都中院立案通知,去銀行交訴訟費時,銀行系統顯示,法院提供的賬號與開戶行不一致,但法院堅稱其提供的賬號沒問題。
陳立雯只好托成都朋友于1月7日登門代交,卻被告知已經逾期。如果真逾期沒有交費的話,就只能算自動撤訴了。
對方辯稱是按文件12月份蓋章的日期算起,陳立雯的脾氣又上來了,“你蓋章當天我就能收到嗎?”
最終,法院收了訴訟費。
至今,陳立雯未敢跟父母透露過她起訴環保局這樣的事情。“自己清楚所作所為有理有據,且在法律框架之內,但我怕我爸媽知道,因為他們與很多普通人一樣,不了解,就會吃驚、恐懼。”
本文轉自《中國周刊》